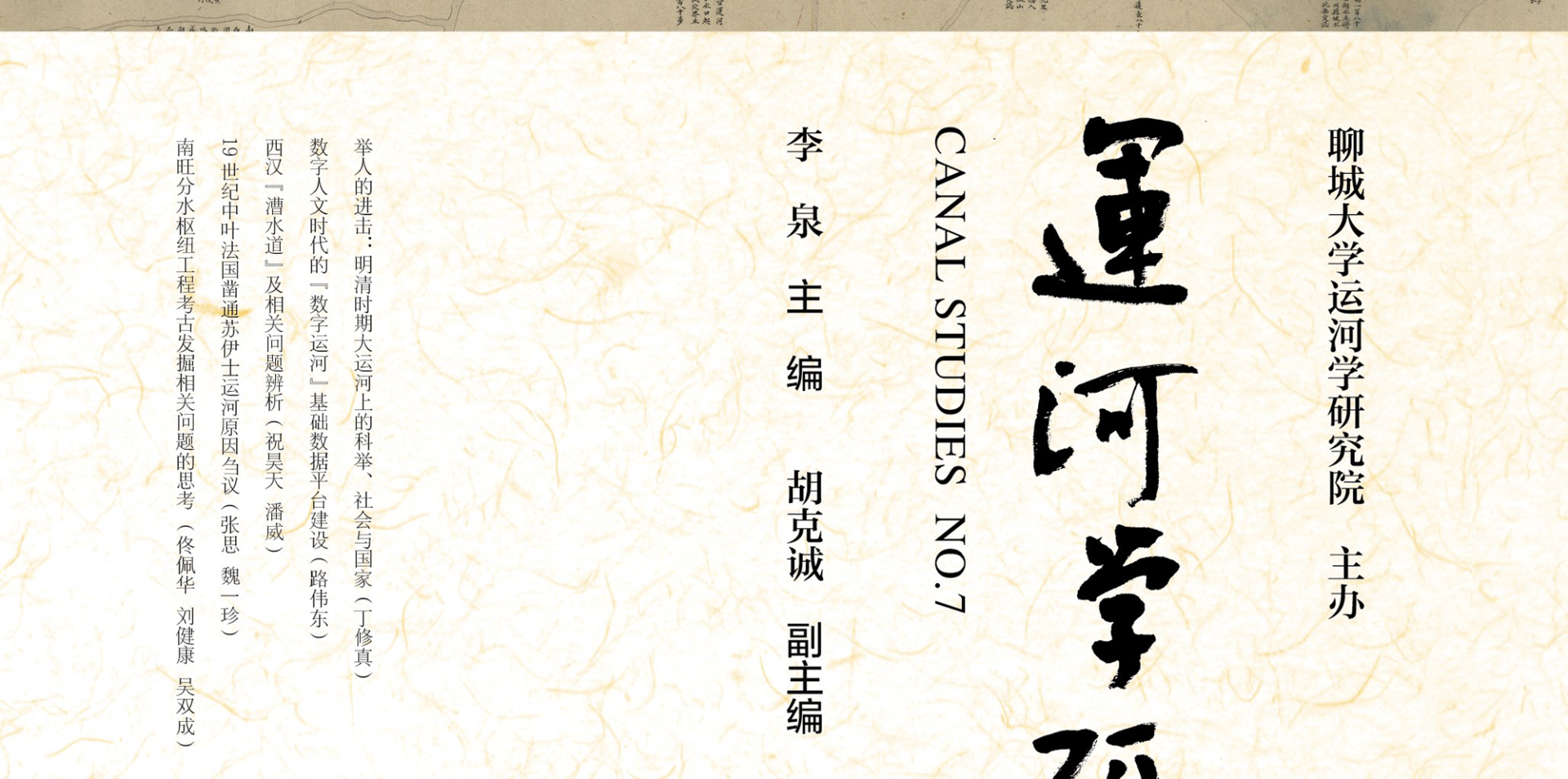长久以来,运河研究一直是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学及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学术关切。近数十年来,随着众多不同专业和学术背景的学者加入,这一主题逐渐被置于不同的学科语境之下,从理论到方法,从问题到叙事,都展现出各异的研究取向。总体来看,传统研究多聚焦于物理形态的运河本体史实考证上,具有鲜明的历史主体性;[1]现代研究则更加关注文化形态上的运河在国家制度运作和地方社会发展框架下的整体性,强调以社会为中心的综合叙事。[2]多样性的个案实证研究在不断丰富并且完善运河研究内涵与外延的同时,也支撑起了理论框架的建构及社会模式的解释,为运河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3]
最近十余年来,随着运河学理论的逐步完善,研究实践出现了向整合性、整体性与细致化结合转向的发展趋势。[4]总体上看,这种研究的转向及其脉络是较为清晰的。但是,由于运河学本身具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属性,研究主题涉及从自然、工程、人文到社会等众多学科领域和研究范畴,学术关切与问题指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肇因于这一学科背景,当前的运河学研究在整合性、整体性与细致化的浮表之下,存在着学术碎片化的系统风险与地方狭隘性的现实困境;另一方面,作为运河学研究核心的传统人文学科,尤其史学及历史地理学突出研究主体的个体性而非集体性,强调具有鲜明个人色彩和明确学术关切的问题导向式研究。这种研究范式下的学术成果固然是建构运河学的重要基石,但运河学发展的最终目标不是谋求一块摆放杂乱物料的平面堆场,而是要建构一座基础牢固的立体学科大厦。很显然,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除扎实的个案研究之外,研究者尤其是机构研究者,必需要认真思考如何整合多源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形成真正具有融合创新能力和创新机制的学术合力。当下扑面而来的数字人文时代,或许已经从理论、技术与方法,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某种可能。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or Ge-Information system, 地理信息系统)支撑的“数字运河”项目无疑是凝聚多学科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共同建造运河学学科大厦的最佳切入点。
一、 不可逆的“数字人文”进程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真正在学术界引起普遍关注,不过最近十多年时间。但如果述其前身,也就是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 Computing in the Humanities)或是人文计量(Humanities Calculate),则可以追溯至20世纪中期。学界一般认为,1949年,意大利神父罗伯特·布撒(Robert Busa)使用IBM计算机为《托玛斯·阿奎纳文集》编制索引的先行工作开启了人文计算的大门。[5]实际上,如果单纯讲人文研究中的计量和统计,其历史则至少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发轫的史学研究科学化探索。尤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的推动之下,利用数学计算模型和数据分析工具生产结构化历史知识的计量史学(Cliometrics)在欧美史学界大放异彩,一度成为最闪耀的学术明星。
但传统人文学者,尤其是历史学者,似乎从一开始就对计量史学秉承一种本能的质疑、排斥、反对甚至是敌视的态度。随便翻检一下,相关的学术讨论、争论甚或是带有强烈个人情绪的公开论战不胜枚举。[6]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计量史学那种通篇弥漫着数学公式与数据图表的研究不符合或者几乎完全偏离了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式。与此同时,也不可否认,相当一部分计量史学研究者于有意或无意间留露出的带有某种数据傲慢和技术炫耀的态度也引发了传统人文学者的厌恶与嫌弃,加剧了彼此的对立,近而造成了沟壑式的学科成见。但是,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计量史学那种过分追求数据、技术与计量的研究往往把复杂综合的历史现象和社会关系全部归结为简单的数学函数关系,用单一的“数据变量”取代了构成历史主体的人的主动历史实践和研究者本人对历史复杂性的整体综合认知和完全个性化全面理解与诠释,由此,最终掩盖了人文和人文研究的光辉。20世纪90年代后,计量史学逐渐淡出主流史学研究者视野的事实,已充分说明了其固有的系统性缺陷。
谈及这一论战,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历史学家往往不由自住的嘴角上翘,带有某种外人不易察觉的胜利的微笑。仿佛当下计量史学宛如明日黄花式的悲惨境遇完全是其不自量力公然挑衅的必然结果。然而,事实上,现实中的计量史学非但没有消亡,反而是在对其固有系统缺陷进行深刻反思[7]的基础上,衍生出了新的学术范式,并深深地根植于传统史学研究之中,成为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在新人口史和新经济史等领域内,[8]计量史学从方法到材料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不但通过数学模型建立起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各种变量要素相互作用和影响的量化关系,而且重构了各种类型的基础数据库,[9]从而使对历史的解释包含了更扎实的数据支撑、更精确的科学计算和更深入的系统分析。“正是基于现代方法的引入和数据材料的发掘,新经济史学对一些已被定性的重大历史事件给出了新的解释和评价,乃至提出了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新结论。”[10]而这也恰恰是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福格尔荣获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11]
人文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有太多主观性、个性化的内容,其本质仍然是逻辑的,思辨的,其主要呈现形式也是具有鲜明个体差异性的文本描述。计量显然不是解决历史学所有问题的终极手段,计量史学也不是历史学的全部和未来。确切地讲,计量史学其实只不过是历史学的一部分,其所解决的问题也只是历史问题的一部分,甚至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但是,不得不承认,计量史学的研究探索的确极大丰富了历史学研究的内涵。
当下蓬勃发展的数字人文(人文计算)与计量史学都以数据为研究基础,都偏重于量化分析的研究手段,学术指向都是人文问题,两者有一定关联,但也有本质区别。近一二十年,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不但引发了全新的技术变革,而且带来了社会结构质的飞跃。当下,以互联网普及与全球化共享为重要标志的信息革命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基础条件是,包括历史文本在内的几乎所有信息开始脱离甲骨、青铜器、竹简、纸质书籍、地图,乃至建筑、雕塑等具象的物质载体,而进入或者即将进入全面的虚拟世界。这是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千万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尽管传统人文学者对人文计算以及数字人文都充满了质疑或者批判,且真正投身其中者数量有限,甚至于热闹喧嚣的数字人文圈内对于什么是数字人文这一最基本的概念问题也存在诸多的争论。但是,毫无疑问,当下扑面而来的数字人文浪潮已经给传统人文研究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实际上,比这种强烈冲击更重要也更严峻的另一个事实是,很多人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们目前已经行进在一个完全不可逆的数字化进程中,再也回不了头了。
二十年前,笔者学术刚起步之时,所做的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跟随前辈学者学习抄录资料卡片,翻看装订成册的研究论文目录,抄录和研究题目相关的论文信息,然后再辗转于图书馆的书架之间,按图索骥,抽选论文所在期刊,简单查阅后,再手工复印后带回细细研读。只不过短短二十年,这样的工作思路似乎已成为石器时代的标准。处于一线的研究者们,回望自己最近十余年的研究经历,自问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迈进过学校或公共图书馆的大门,多久没有踯躅在书架和泛黄积灰的图书之间,是我们停止学习,不再前进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实事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进出那个网上的数字图书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捷方便地获取并阅读需要的文献,洞悉并了解最新的学术前沿。人类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信息全面虚拟化,推动了信息的存储方式、传播途径以及分析手段都发生了质的改变。这是当下数字人文或人文计算与之前史学家们所理解的计量史学最根本的时代背景区别。数字人文不再仅仅是简单的用数学工具处理史学研究中的人口、地亩、税赋、道路、兵马、钱粮等狭义的数据,而是整个人文研究中更广义的历史文本、研究方法及研究指向全面数据化呈现。
由此延伸,“数字人文不仅革新了人文研究的范式,还意味着全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和知识交流模式。”[12]比如,在信息全面数字化的基础上,综合知识推理、自然语义处理、人工智能以及语义网络等多方面技术,更容易生成可视化的知识图谱,更容易建立信息间的复杂链接,从而实现数据的深度挖掘。[13] CBDB的“宋代文人通信网络”已经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极有趣的案例。[14]当前语境的数字人文虽然仍处于初创萌芽期,离最终的目标还相距甚远,并且仍有部分数字人文研究者重复着当年计量史学研究者那种“每个研究者都应该是程序员”式的技术傲慢,但从知识生产转型的角度讲,数字人文其实是中外人文学者在全球近数十年大规模纸面文本数字化实践基础上于当下数字语境中的共同研究自觉,[15]
二、 “数字运河”的概念和框架
1998年1月,时任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在加州科学中心开幕典礼上发表演说,首次提出了“数字地球”的概念。自此开始,“数字城市”、“数字交通”、“数字金融”以及“数字图书馆”等不同尺度和不同维度上的数字化概念纷纷出现,并迅速经历了从理论研究、工程建设到场景应用的快速呈现。这其中,作为“数字地球”在流域尺度上应用的“数字流域”,同样取得了飞速的发展。[16]在国内,最具代表性的“数字流域”项目非“数字黄河”[17]与“数字长江”[18]莫属。两者都是国家层面的重大数字工程,均经历了近二十年的长期发展,完成了从基础数据、模型模拟到应用决策三个自下而上阶段的工程建设,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与之相比,对于“运河”这一重要的地表水体,不论在学术层面还是政府层面均鲜有关注,不但没有开展相关的总体框架研究和系统设计,甚至于到现在为止,连最基本的“数字运河”概念都没有提出。[19]
“数字运河”是数字人文时代运河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那么,什么是“数字运河”呢?借鉴“数字黄河”、“数字长江”的相关研究成果,简单的讲,就是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构建的运河全流域多要素一体化综合数字集成平台和虚拟环境。“数字运河”以数据为关键要素和核心驱动,通过功能完善的数据仓库、应用软件系统和专业模型系统等,对运河基础数据进行数字化采集、存储、模拟和分析,并在Web可视化环境下实现数据迭代和资源共享,并由此衍生出一整套数字人文环境下重新定义和回答运河学术问题和现实关切的新方法、新手段和新范式,从而增强运河研究的便捷性、科学性和中心性,最终为运河学的学科发展及流域开发、保护与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和智力支持。
“数字运河”属于“数字流域”的范畴,但与“数字黄河”、“数字长江”等国家工程层面的“数字流域”项目重点聚焦防洪减灾、资源调配、水土保持、工程建设、政务管理等现实应用,强调时效性、预见性和科学性不同,当下的“数字运河”建设应该更加偏重于基础数据的整合与集成,强调学术性和研究性,尤其需要突出其历史的主体性。这种明显的差异主要源于运河本身的特质。运河是人工形塑的水道,是重要的地表人文景观,用以连通不同的地域和水域,其成因、走向、水文、职能以及河工、管理和使用等都与自然河道显著不同。历史时期开挖的很多运河,早已湮废毁弃,或成为历史的遗址遗迹,或仅隐现于历史文本之中。部分运河即使留存至今并仍然使用,但在当下人文地理环境之中,其原来之所以开挖的特定背景及核心职能也大都早已不复存在,由此成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但运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曾经发挥过的重要作用远非仅仅是行舟挽运这一现实功能本身,实际上,“以运河为载体或者伴生的运河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标签。作为一个复杂系统,运河连接与传承的不仅是地域意义上的南北,地理意义上的水系,经济意义上的市场,政治意义上的漕运军政,社会意义上的人群生活,文化意义上的艺术、风俗等内容,而且其自身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运行与表现方式。”[20]正是基于这样卓越的建设成就、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大运河”这一中国运河建设最杰出的代表才在2014年成功入选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对于这样一个极具历史性的地理实体进行数字化建设,首先应该强调基础历史空间数据、历史文献和研究成果整合的统一性、标准性和集成性,其目的是服务以大运河为核心的整个运河的研究、保护和利用,最终目标指向是“运河学”学科建设支撑平台。
基于以上原因,“数字运河”项目的总体框架虽然与“数字黄河”、“数字长江”等其他“数字流域”大体相似,也可以划分为基础设施、应用服务平台和应用系统三层架构,[21]但因为现实需求和应用场景等差异,侧重点有所区别。三层架构中,基础设施主要是用于数据采集、存储、管理和分析的各类软硬件系统,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器、工作站、磁盘阵列等硬件,用于数据处理、分析的专业软件和构建三层C/S、C/S和B/S混合软件体系[22]的运行环境;应用服务平台主要由各类基础数据库、专业数据库、知识库及模型库等各类服务中间件构成;应用系统则是在应用服务平台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用于服务特定应用场景的专业系统。与“数字黄河”侧重于第三层应用系统解决现实关切不同,服务运河学研究的“数据运河”建设应该把重心放在第二层的应用服务平台上。具体的讲,就是搭建应用系统的开发和集成环境,建设标准的基础数据库、信息数据库、模型库和知识库等,实现运河数据的统一管理和高度共享,有效避免或解决数据孤岛问题,提高数据利用的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信息处理逻辑、应用处理逻辑等,从更深层次上发掘数据的可利用价值,最终为运河学学科建设提供数据和平台支撑,为现实的大运河保护及运河流域开发提供智力支持。
三、 “数字运河”建设的基础内容
运河是现实客观存在,或者曾经历史客观存在的地理实体,当下在运河研究、保护、利用与开发过程中形成的完整的运河学理论与方法,不论是具体探讨运河开挖、运维对其所处自然环境的影响,与区域社会人群的关系,还是阐述作为制度与历史现象的运河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价值与意义,从根本上讲,所有这些问题与关切都是在物理形态的运河水道基础上发展衍生出来的。因此,“数字运河”的基础实际上是物理运河的虚拟对照,首先需要构建全数字化的运河历史地理空间数据平台,提供运河本体的地理定位、关系描述、属性表达以及空间分析等,以此作为空间载体,才可以开展运河文献集成、文本数据挖掘、知识图谱建立、信息处理逻辑、数学模型分析以及应用系统开发等工作。基于此,当下开展“数字运河”建设,首先要做的关键工作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运河基础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地理空间里的运河实体形态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因此,对于运河地理信息的探讨应该在历史的语境中进行解读。中国运河基础历史地理信息数据的源头主要是历史文本文献和计里画方式或山水画式的历史地图,传统沿革地理学者及当代历史地理学者对这些历史文献中记载的运河走向、兴废和演变等基本信息都做过较为系统的考证和研究,由此形成了较为标准化的文本记录。自1950年代开始,在以谭其骧先生为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研究团队的示范和带动下,这些文本形式的运河标准历史地理信息被逐渐纳入到现代西方地理学的科学体系之中,成为以测绘地图为底图的中国历史地图上的基本地理要素。
至1990年代中期,随着GIS逐渐走出实验室,进入到普通研究者尤其是传统人文社科研究中来,纸本测绘地图记载的运河历史地理信息数据又经历了逐步数字化的过程,最终形成了一系列标准的GIS数据。[23]这其中,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ese Historical GIS, CHGIS)项目在中国传统历史地理信息的数据模型、数据存储以及数据分发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项目中使用的“生存期”概念,成功的解决了在历史地理信息记录中同时把握时间和空间两个尺度变化的难题,[24]准确描述这些信息在时间上的连续变化,而非是一个或多个时间截面的孤立呈现。[25]其成功经验和工作方案可为处理运河历史地理信息提供借鉴。
现代运河基础空间数据主要来源于大比例尺实测地形图和航拍或卫星遥感影像数据(Remote Sensing Image, RS)。地形图主要是民国以来中国官方实测图及日、美等外国势力偷测或改绘图,其中如《中国大陸五万分の一地図集成》(日本科书院,1998年,影印)、[26]美国陆军工程署陆军制图局25万分之一中国地形图等(AMS, 1950’s)[27]等,都比较容易获取。195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及地方测绘部门实测的更高比例尺地图,也可以有条件取得;遥感数据主要来源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的DEM数据,如SRTM DEM 90M,Aster GDEM 30M等,可以很方便的免费获取,更高精度的米级甚至亚米级数据也可以通过公开的商业渠道获得。这些数据时间截面大部分都在2000年以后,可以与地表形态被大规模工业化形塑前的实测图形成互补。
这些多源运河基础空间数据在提取其空间变化的出生、改名、改建及死亡等时间节点后,经过GIS软件配准后,最终可以获取并可视化比较完整的低分辨率的线状运河,中分辨率的面状运道以及高分辨率的闸坝等运河历史地理信息,从而用数字展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运河实体形态变化。在部分地区,可以借助大量影响资料丰富对运河历史的情景理解,也可以根据运河实际形态,可以构建高精度的两维或者三维河道形态,并实现闸坝工程的虚拟融合。按照CHGIS定义的数据模型,使用“生存期”的方法,可以方便准确地记录每一条运河及每条运河不同区段的空间信息属性息,时间序列、继承关系以及隶属关系等,从而建立“数字运河”基础空间信息数据库。
其二,运河基础历史文献信息系统。包括运河文献在内的流域历史文献数字化其实是“数字图书馆”的自然延伸,起步比较早,从事相关研究种者大都具有图书信息管理学的背景,且大多聚焦技术和标准层面的设计,这点从“数字黄河”与“数字长江”的建设中可以看得很清楚。[28]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陈力在2016年的一次运河学笔谈中建议,对运河文献应该“建立数据库进行管理、服务。同时,还要重视对元数据的整理与编纂,采用国际数据标准,能够被百度等检索到,使其更具开放性与规范性。”[29]与之不同,历史学者的运河文献关切更多聚焦在文献本身梳理和研究的学术痛点上。运河学科本身的交叉性,使得其知识体系虽然内涵清晰,但内容却丰富庞杂,支撑文献零散芜杂。除少量历代运河专书外,其他相关文献大多隐现于不同的学科门类之下,分散于不同的收藏部门。[30]这给运河学者们收集、整理和使用文献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如果仅从理论和技术上来讲,基于目前网络环境共建共享可扩展的分布式知识网络系统,可以用数字技术存储不同载体和地理位置的信息资源,并实现跨区域、面向对象的网络查询和传播。但在实际中,需要真正获取数据时,却又面临重重困难和各种制约。互联网以及数字人文时代的来临,使得研究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便捷地接近或者获取自己的研究文献和研究数据,似乎传统时代研究者曾经面对的那种几乎无法克服的文献资料重重黑幛顷刻间就被一扫而光,但实际上,数字人文时代的数字鸿沟,隐藏在各类数据库和平台的账号权限之后,不但仍然存在,而且还有日益加剧之势。因此,构建“运河历史文献信息系统”,形成真正的“数字运河”数据中心,必须切实加强基础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在李泉教授看来,运河文献“系统地搜集整理上述资料,非一人一时所能完成。一方面,从事运河研究的同仁务必将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作为学术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努力搜求研究各个方面的历史资料;另一方面,从事运河研究的学术机构更应集合大家的力量,有组织、有计划地搜集整理上述资料。”[31]这样的提议虽然颇具无奈意味,但却切实可行,实际上,这对于建设运河基础历史文献系统也几乎是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案。
任何历史事件和文化要素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都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都是具有时间属性的空间数据。根据运河文献和数据产生的时空背景、涉及具体内容提可以提取相关的时间和空间信息,从而与基础空间数据关链在一起,形成统一的数据库,并构成最终的“数字运河”数据中心。
四、 最终的指向和目的
在数字人文时代来临的当下,开展 “数字运河”建设,可以为打造运河学研究的资料中心、数据中心、教学中心和研究中心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进而可以夯实运河学科的研究基础,丰富运河学科的研究内涵,有力推动运河学科的整体全面发展。在构建独立自主运河大数据的基础上,通过不断丰富数据容量,优化机器学习算法,进行具有更加深度的文献挖掘,以图发现蕴藏在海量数据之中大量未知的和有价值的信息,减轻研究者从事低层次信息处理和分析的负担,从而使研究者更加专注于需要学术智慧和问题关切的研究工作本身,最终提高运河学科研究质量和学术水平。“数字运河”的建设会带来新的问题关切、知识体系和研究范式。其实,这正是数字人文本质,也是与传统人文计量的最大区别。
如果说,运河基础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是构建“数字运河”的骨架,运河基础历史文献信息系统便是构建“数字运河”的肌肉,那么构成“数字运河”灵魂是什么呢?实际上,建设“数字运河”学术意义不在于谋求简单的基础空间数据的可视化、纸本文献的数字化以及非结构文本信息的结构化,[32]也不是单纯追求数据规模的增长、集成以及整合,而是要在重建一个宏观上帝视角与微观现场视角并存的沉浸式数字化运河历史景观的基础上,尝试理解不同历史语境和不同学科语境下的运河究竟曾经是一种怎样的历史存在。 原文载《运河学研究》第七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2月,第66—78页。
[1] 邹逸麟:《历史上水利工程的环境问题值得关注》,《运河学研究》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2页。
[2] 吴欣:《从“制度”到“生活”:运河研究的新维度》,《光明日报》2016年8月10日。
[3] 罗哲文:《运河申遗应建立运河学》,《中国文化遗产》2011年第1期;李泉:《运河学发微》,《运河学研究》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32页。
[4] 吴欣:《“大运河”研究的学术进程及问题意识(2014~2018)》,《运河学研究》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10页。
[5] 林施望:《从“人文计算”到“数字人文”——概念与研究方式的变迁》,《图书馆论坛》2019年 第8期。
[6] 随便翻检一下,相关的学术讨论甚或公开的论战数不胜数,比如张仲民与金观涛、刘青峰的讨论就很有代表性。详请参见张仲民:《数据库与观念史研究》,《上海书评》2010年5月23日;金观涛、刘青峰:《简答张仲民先生对拙作的评论》,《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5月30日;张仲民:《观念史研究应该怎么做——— 再次回应金观涛、刘青峰两教授》,《南方都市报》2010年9月5日;《就观念史研究再答张仲民先生》,《南方都市报》2010年9月19日。
[6] 夏翠娟:《面向人文研究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试论图书馆学对数字人文的方法论贡献》,《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年第3期。
[7] 吴承明:《谈谈经济史研究方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1-182页。
[8] 江立华:《西方人口史研究新进展述评》,《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
[9] 吴裕宪、王雅玲:《建设中国经济史数据库群的探索》,《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
[10] 朱富强:《计量重构历史中潜含的历史虚无主义:主流计量史学的逻辑缺陷及其批判》,《学术研究》2019年第7期。
[11] 1964年,罗伯特·福格尔的《铁路和美国经济增长:计量经济史学论文集》(Robert Fogel. 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Econometric History.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4)出版,标志着“历史计量学”(也被称为“新定量经济史学”)的诞生。
[12] 夏翠娟:《面向人文研究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试论图书馆学对数字人文的方法论贡献》,《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年第3期。
[13] 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CiteSpace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科学研究》2015年第2期。
[14] CBDB的宋代文人通信网络就是一个很好数据挖掘的案例。参见包弼德:《群体、地理与中国历史:基于CBDB和CHGIS》,《量化历史研究》2017年Z1期。
[15] 陈静:《当下中国“数字人文”研究状况及意义》,《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
[16] 庞树森、许继军:《国内数字流域研究与问题浅析》,《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2012年第1期。
[17]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数字黄河”工程规划概要》,《中国水利》2003年第5期。
[18] 熊忠幼、张志杰:《实现“数字长江”宏伟构想》,《中国水利》2002第 4期。
[19] 以“数字运河”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进行跨库检索,相关研究成果几近空白,很显然,目前这一工作还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李孝聪教授在2016年的一次运河学笔谈中曾提到“运河学的数字化建设”问题,惜未展开讨论。相关内容可参见《运河学笔谈:运河学研究方兴未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6月8日。2004年和2008年,无锡和天津两地先后建成一南一北两座“大运河数字博物馆”,中国数字科技馆也推出了“漫游大运河”的网站(http://b2museum.cdstm.cn/canal/)。这些工作虽然都涉及运河数字化的部分内容,但其实质仍然是数字化虚拟博物馆的实践,大都偏重于使用3D虚拟数字画面及多媒体互动技术动态展现京杭大运河的历史面貌,或通过使用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VR)或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AR)等数字科技手段,实现大运河全境的虚拟现实仿真,从而让观众有更多沉浸式的观看体验,整体上属于新媒体、全视角、交互式的文化创新项目,与数字人文时代的“数字运河”基础数据平台有本质的区别。零星资料显示,清华大学曾经启动过“数字化运河”项目,并研发了相应标准规范、关键技术和软件系统,其目的主要是京杭大运河沿线遗址与文物的调查保护,由于缺乏更多公开信息,具体细节不得而知。相关内容可参见赵云:《文化遗产数字化展示研究》,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7-28页。近年来,云南大学潘威副教授带领学术团队从事“数字历史黄河“工作,最终成果将包括专业历史资料管理平台、专题数据集和历史信息分析和展示功能(潘威:《“数字人文”背景下历史地理信息化的应对——走进历史地理信息化2.0时代》,《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作为”数字历史河流“的探索实践,”数字历史黄河“工作对于”数字运河“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0] 吴欣:《运河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与知识体系》,《人文杂志》2019年第6期。
[21] 李景宗; 寇怀忠:《“数字黄河”工程建设的现状与未来发展》,《人民黄河》,2011年第11期。
[22] 牛冀平、胡志华、肖晓红:《数字流域系统的C/S与B/S混合软件体系结构》,《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
[23] 路伟东:《CHGIS数据模型与千年尺度完整时间序列空间基础数据——以1912年至1949年县级治所点数据为例》,《历史地理》第3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69-279页。
[24] Donna J. Peuquet, “Making Space for Time: Issues in Space-Time Data Representation”, GeoInformatica, 2001, Vol.5 (1), pp.11-32.
[25] 满志敏:《走进数字化: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历史地理》,第18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22页。
[26] 邓发晖:《<中国大陆五万分之一地图集成>研究–兼论中国近代以来的军事测绘(1903~1945)》,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8年硕士论文。
[27] University of Texas Libraries: http://legacy.lib.utexas.edu/maps/ams/china/
[28] 邢琳:《黄河档案信息数字资源系统建设研究》,《创新科技》2016年第11期;代君、纪昌明:《面向共享需求的“数字流域”中信息资源的组织》,《情报杂志》2006年第4期。
[29] 陈力:《运河学笔谈:运河学研究方兴未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6月8日。
[30] 运河基本文献大致分为基本文献、档案与民间文献三类,详细梳理、分布及收藏见吴欣::《运河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与知识体系》,《人文杂志》2019年第6期。
[31] 李泉:《中国运河文献资料的分类整理》,《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32] 朱本军、聂华:《互动与共生:数字人文与史学研究——第二届“北京大学数字人文论坛”综述》,《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年第4期。